|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县城的公交车少之又少。那时,人们外出大都骑自行车,公交车站点也不多,简易的站牌在路边傻呆呆站立。 当时的公交车分两种: 一种是平头,车身较长,小窗户大车身,座位不多,跑起来像是患哮喘病的老人,上坡跑着很吃力,车后冒着黑烟,站牌候车的人老远听到这“哮喘”声,就知道公交车来了。及至跑到站牌下,公交车“嘎——”地一声停下,只听“呼咚”一声,门开启,有时,需要人工开启车门。人们挤在车门里动弹不得,常常是还没等车里人下车,上车的人都争先恐后往车里挤,挤不上车的,只好任风吹雨淋等下一班车了。 还有一种车是“连体”客车,也就是俗话说的“两节鞭”式的,一次能容纳100多人,乘坐这样的车,大家都不喜欢站在中间位置,担心转弯时,会被甩一边去。
车厢里的乘务员统一着装,面带微笑,胸前挂着一块木板,木板上有车票,车票一指宽,还有线绳牵的圆珠笔。她们麻利地收下一元钱,放在挎包里,提笔“唰唰”地在薄纸车票上写着乘车时间和地点,忙的时候还会将写好的车票放嘴里咬着。有时,车厢里人多,乘务员还要维持车里的秩序,不时地喊道:“请往里面走,请往里面走……”服务员凭着记忆大体能记得谁买票,谁没买票。夏天,车厢里没有空调,温度高,加上人多,乘务员往往累得满头汗水。早晨上车时,头上梳着的两个小辫子,晚上下班时,头发是散乱的,喉咙也哑了,说不出话。因此,乘务员水杯里大都泡着胖大海喝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我在城郊一个村子蹲点工作,恰逢公交车延伸到城郊周边村。每天来往村里,都要乘坐公交车。女乘务员20岁的样子,梳着两个小辫子,瓜子脸、双眼皮,笑时还有两个小酒窝。她晓得我们是常客,下午最后的一个车次,她就在村子等我们上车。时间长了,我们也不好意思让她久等。她却说:“你们给老百姓跑腿办事儿,我们公交车稍等一会儿也是应该的。” 一天,我乘坐公交车往村里赶去,谁知,天公不作美,半路突然下起雨来,瓢泼大雨下个不停。通往村子的土路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的,本来平坦的路面积了一湾湾的水。公交车停在村口,司机瞧瞧道路,摇摇头,意思是不能往前开了。离所住的村子还有一段路程,雨越下越大,这可怎么办?正当我们犯愁时,忽然有人在我身后递来一把雨伞,转头瞧是那个乘务员!她向我莞尔一笑。我撑着雨伞往村里走去。雨后,所住的村子好长时间也没通公交车,村委只好找人把坑坑洼洼的路面给铺平了,公交车这才进了村子。 后来,荣成实行“村村通”公路改造,路面硬化了,公交车行驶顺畅了许多。城市里的公交车也多起来,人们出行方便了。乘务员热情周到,人们进城购物也更加便利。 就在前几年,城里公交车“大变脸”,全是清一色的现代化绿色节能客车。这种车噪音小、容纳客人多,车厢里设有空调和孕妇、老人专用椅子。有的公交车还是两层车厢,人坐在上面,可将城市风光一览无余,一次花上几元钱,可以直达荣成各大风景名胜区。乘务员热情接待乘客,喇叭里不时地提醒乘客:现在到哪里,下站到哪里…… 没过多久,公交车又变样了,偌大的车箱里,只有驾驶员一人,实行了无人购票的新跨越。
公交车不断翻新“蝶变”,而那些昔日漂亮的女乘务员哪去了?有一天,有位女司机师傅娴熟地驾驶公交车,我仔细端详:瓜子脸、双眼皮,笑时还有两个小酒窝......哎呀,这不是当年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的乘务员吗?我猜想,她应该是20几岁孩子的妈妈了。
|

 手机版
手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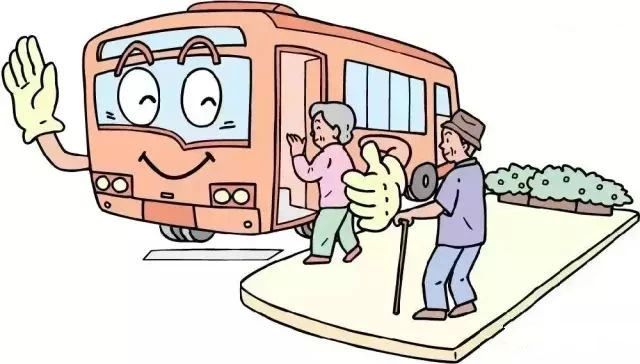








 鲁公网安备 37108202000325号
鲁公网安备 37108202000325号





